中外双边投资协定对香港的适用问题
本作品内容为中外双边投资协定对香港的适用问题,格式为 doc ,大小 28160 KB ,页数为 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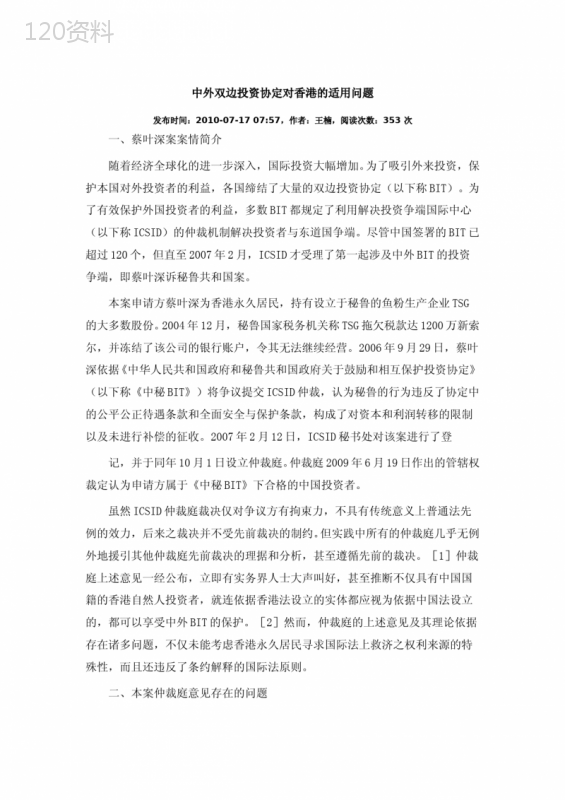
('中外双边投资协定对香港的适用问题发布时间:2010-07-1707:57,作者:王楠,阅读次数:353次一、蔡叶深案案情简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国际投资大幅增加。为了吸引外来投资,保护本国对外投资者的利益,各国缔结了大量的双边投资协定(以下称BIT)。为了有效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多数BIT都规定了利用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以下称ICSID)的仲裁机制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尽管中国签署的BIT已超过120个,但直至2007年2月,ICSID才受理了第一起涉及中外BIT的投资争端,即蔡叶深诉秘鲁共和国案。本案申请方蔡叶深为香港永久居民,持有设立于秘鲁的鱼粉生产企业TSG的大多数股份。2004年12月,秘鲁国家税务机关称TSG拖欠税款达1200万新索尔,并冻结了该公司的银行账户,令其无法继续经营。2006年9月29日,蔡叶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以下称《中秘BIT》)将争议提交ICSID仲裁,认为秘鲁的行为违反了协定中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和全面安全与保护条款,构成了对资本和利润转移的限制以及未进行补偿的征收。2007年2月12日,ICSID秘书处对该案进行了登记,并于同年10月1日设立仲裁庭。仲裁庭2009年6月19日作出的管辖权裁定认为申请方属于《中秘BIT》下合格的中国投资者。虽然ICSID仲裁庭裁决仅对争议方有拘束力,不具有传统意义上普通法先例的效力,后来之裁决并不受先前裁决的制约。但实践中所有的仲裁庭几乎无例外地援引其他仲裁庭先前裁决的理据和分析,甚至遵循先前的裁决。[1]仲裁庭上述意见一经公布,立即有实务界人士大声叫好,甚至推断不仅具有中国国籍的香港自然人投资者,就连依据香港法设立的实体都应视为依据中国法设立的,都可以享受中外BIT的保护。[2]然而,仲裁庭的上述意见及其理论依据存在诸多问题,不仅未能考虑香港永久居民寻求国际法上救济之权利来源的特殊性,而且还违反了条约解释的国际法原则。二、本案仲裁庭意见存在的问题⒈未能考虑香港永久居民国际法上某些权利的特殊来源。本案仲裁庭认定申请方属于受《中秘BIT》保护的中国投资者的主要依据是协定第2条第1款,该款规定“投资者”一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拥有其国籍的自然人…”。申请方提供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以及经公证后的文件足以证明其出生于福建省,父母均为中国国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以及人大常委会对该法在香港实施的解释意见,应认定申请方具有中国国籍。无论是《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以下称《ICSID公约》)还是《中秘BIT》都没有明确将具有中国国籍的香港居民排除在其适用范围之外。申请方既然已经被认定具有中国国籍,自然受《中秘BIT》的保护。[3]仲裁庭称其“只须认定本案申请方是否有权根据《ICSID公约》及《中秘BIT》将与其在秘鲁共和国的投资有关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为此,没有必要认定《中秘BIT》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也不属于本案仲裁庭需要分析的问题。”[4]而且“就算《中秘BIT》不适用于居住在香港的秘鲁人,也不必然令居住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不受BIT之保护”。[5]通常BIT除了规定缔约一方投资者及其投资在缔约另一方享有的实体权利(如最惠国待遇和公平公正待遇)之外,还往往赋予投资者在国际法上的程序性权利,即将其与缔约另一方之间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取得国际法上的救济。此外,BIT的保护对象是在缔约一方领土内投资的缔约另一方的投资者及其投资,亦属于涉及领土适用范围的条约。很多BIT本身就包括了空间适用范围条款或者专门规定了“领土”一词的定义。不难看出,本案仲裁庭在刻意回避《中秘BIT》是否适用于香港的问题,试图割裂BIT对香港空间的适用和对香港永久居民的适用之间的必然联系。仲裁庭将其考查的重点放在申请方的中国国籍上,认为只要是中国公民,无论其居住在何地,都符合第2条第1款的要求。然而,在国际法上某些权利及其来源方面,具有中国国籍的香港永久居民与其他居住在国内外的中国公民并不完全相同。毫无疑问,本案申请方蔡叶深具有中国国籍,但其持香港特区护照,是香港永久居民。而仲裁庭并未就此进行深入考察,整个管辖权裁定仅使用“香港居民”的表达方式。然而“香港居民”与“香港永久居民”两者的含义并不相同。仲裁庭将两者混为一谈为其随后的错误分析埋下了伏笔,虽失之毫厘,却谬之千里。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称《基本法》)第24条,香港居民包括永久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在一国两制的架构下,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不仅体现在其所实行的社会制度和内部事物方面,还体现在其对外关系的某些方面,这也包括具有中国国籍的香港永久居民享有的某些国际法上的权利及其直接来源。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个人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作为国际法的主体,享有国际权利。[6](p5-6)正如国际常设法院就关于但泽问题法院管辖权案件的咨询意见所称,“国际法并不阻止个人直接取得条约上的权利,只要缔约国有此意图”。[7]一般来说,国籍是个人和国际法间的联系。香港永久居民作为个人,其在国际法上享有的权利,必须经过主权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约或承认产生。[8](p162)不过,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第153条,在回归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议并不必然适用于香港,而是由中央人民政府根据香港特区的情况和需要,在征询香港特区政府的意见后再行决定。然而,1997年6月中国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的外交照会附件所列的适用于香港特区的条约中并未包括1994年签订的《中秘BIT》,而中央政府也未经咨询香港政府的意见后,将《中秘BIT》适用于香港特区。因此,本案申请方蔡叶深不应基于《中秘BIT》主张其在国际法上享有的权利,将其与秘鲁政府的争议提交ICSID仲裁。《基本法》第151条授权香港特区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1997年7月7日,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区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转交了中国外交部长的授权函,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已授权香港特区在促进和保护投资等领域与有关国家就双边协定展开谈判。这表明除非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基本法》第153条规定的特别程序,令中央政府缔结的国际条约适用于香港特区,否则香港永久居民在投资促进和保护方面取得国际法上的权利应直接经香港特区缔约产生,而非因中央政府缔约产生,即便此类权利的最终来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案申请方作为香港永久居民,只能通过香港政府缔结的条约取得将争端诉诸ICSID仲裁的有关权利。⒉未能分析其条约用语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本案仲裁庭仅仅机械地考查了《中秘BIT》第2条第1款的一般意思,忽视了缔约方的原意。该款的字面意思似乎表明协定适用于所有中国公民,但有关条约解释的国际法规则却并未完全排除某些条款的用语可能具有特殊意义。尽管《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条约解释的问题上基本采纳了客观解释(约文解释)的主张,但强调缔约方原意的主观解释并未被完全抛弃。第31条第4款规定“倘经确定当事国有此原意,条约用语应使其具有特殊意义”。虽然现有国际法规则并未就如何认定缔约国的此原意提供有效的指引,不过,从缔约时的情况,缔约方的实践等方面都不难看出中秘两国不欲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拥有其国籍的自然人”包括具有中国国籍的香港永久居民。⒊未能认识到可以通过默示的方式限制条约的适用范围。沿着割裂BIT对香港永久居民的适用和对香港空间的适用的错误思路,仲裁庭又指“被申请人未能充分证明《中秘BIT》缔约双方有意将香港居民排除在其适用范围之外。如果双方存在上述意愿,就应该通过明示的例外条款进行规定。”[9]然而,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则,对条约适用范围的限制并不仅限于明示的例外条款。《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9条规定:“除条约表示不同意思,或另经确定外,条约对每一当事国之拘束力及于其全部领土。”这表示对条约的领土适用范围,首先要考虑当事国的意思,只有在没有此类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条约的效力才原则上及于当事国全部领土。“如果从条约的性质来看显然不适用于缔约国的所有领土,但又缺少领土条款或明确的说明,一项确立的实践是由国家决定其适用的地域范围。”虽然《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没有专门的条款谈及条约对缔约国有关个人的适用问题,但第29条已经反映出缔约国若要限制条约的适用范围(无论是对人的适用还是对领土的适用),除了像仲裁庭所说的那样通过明示的方式作出,还可以通过惯常实践以默示的方式将部分国民或领土排除在条约的适用范围之外。尽管《中秘BIT》并没有明示的例外条款,但中国、秘鲁以及香港的有关实践已经充分表明缔约方已经用默示的方式将具有中国国籍的香港投资者不属于《中秘BIT》保护的中国投资者,并将香港特区排除在其适用的空间范围之外。三、体现缔约方原意的有关实践⒈缔约时的情况。新中国始终认为香港是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承认“割”、“租”香港的中英《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1997年7月1日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不代表自此日香港才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缔结的包括《中秘BIT》在内的所有国际条约都未规定明确的条款将香港排除在其空间适用范围之外。但事实上,在中国政府尚未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前,是由英国负责香港的对外关系。国际条约在香港的适用离不开英国的缔结、参加或授权。英政府决定其参加的国际条约是否延伸适用于香港,或由香港政府基于英国授权成为某些条约单独的缔约地区。就BIT而言,英国通过“领土延伸换文”将其签订的某些BIT适用于香港。蔡叶深案所涉及的《中秘BIT》签订于1994年6月,当时中国尚未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因此即便没有明确规定排除条款,该协定对香港也不适用。就条约对个人的效力而言,中国政府并不承认香港同胞就因香港未处于中国的有效的管理之下而自动失去其中国国籍。但根据英国国籍法,香港原居民和在香港出生的人士也曾被认为属于英国公民。实践中,他们在国际上亦受英国的保护。根据1948年英国国籍法,在该法生效之日起出生于香港的任何人都是“英国及殖民地公民”。1981年英国国籍法废除了英国及殖民地公民身份,所有凭香港关系取得英国及殖民地公民身份,又或者在1983年1月1日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人士,皆成为“英国属土公民”。英国缔结的某些BIT在定义自然人投资者时也涵盖了英国属土公民,这时持英国护照的香港居民则可以享受有关BIT的保护。虽然《中秘BIT》规定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都可能成为合格的投资者,但在香港回归之前,持英国护照的香港居民并不能寻求其保护。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更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赏。根据该原则于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以及1990年公布的《基本法》都规定香港在回归后可以在经济、贸易等领域单独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条约并不必然适用于香港。《中秘BIT》签订于1994年,晚于上述日期。不难推定秘鲁对即将缔结的协定在97之后并不必然适用于香港投资者以及香港特区是了解的。中国则更不可能意在令《中秘BIT》不经特殊程序而在回归之后直接适用于香港特区和香港永久居民,否则不仅会违反同样作为双边条约的《中英联合声明》以及作为香港宪法性法律的《基本法》,更破坏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构想。⒉中国和秘鲁有关缔约实践。正如英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奥斯特所说:“1996年6月30日午夜将香港移交给中国的情况是独特的,并没有提供太多调整更一般条约问题的方法。”《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第15条所确认的“移动的边界原则”并不适用于香港回归后的条约适用问题。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情况与一般的部分领土转移有所不同。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中国政府始终不承认“割”、“租”香港的不平等条约。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下,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可单独同各国、各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并在经济、贸易等单独地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对于中国缔结的国际条约如其适用范围包括香港,中国政府往往会通过明示的方式作出。例如,2005年,中国政府在世界卫生大会上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国际卫生条例(2005)》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境,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在回归之前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亦专门就国际条约在香港的适用问题达成一致。根据《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二的规定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就在回归后继续适用于香港的多边条约达成一致。但上述协议仅对双方有拘束力,无法解决与条约其他缔约方的国际条约关系问题。参照《条约继承公约》有关条约继承的具体做法,1997年6月20日,中英两国分别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外交照会,在附件中列出了将在回归后继续适用于香港的条约,并向各项条约的保管机关发出照会。但这些继续适用于香港的国际条约都是多边条约。尽管《中英联合声明》并未规定英国缔结的曾适用于香港由英国缔结的双边条约(包括BIT)在回归后不得再适用,但由于双边条约具有契约性的特点,往往与缔约双方的国内经济法律政治制度相关,联络小组协议决定所有英国缔结的曾适用于香港双边条约在回归后全部停止适用。尽管香港回归后仍保留了之前适用条约的传统,即条约必须转化香港特区本地法律才能适用,但有的双边协定则是通过在政府宪报上刊登后即生效的适用方式。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只有极个别的中外双边条约经咨询香港政府意见并取得缔约方同意后适用于香港特区。例如中国与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英国、越南等国签订的领事条约或领事协定。在实践中,对于某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向我国提出的有关双边条约适用于香港特区的疑问,外交部条法司的答复主要是依据《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有关规定作出解释。然而,并未有任何中外BIT通过《基本法》第153条规定的程序而适用于香港。秘鲁政府的嗣后实践也表明中秘两国不欲将《中秘BIT》适用于香港。2008年11月20日与香港签订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合作安排》之后,秘鲁又于2009年4月28日同中央政府签订了《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其中第十章涵盖了《中秘BIT》的主要内容。该协定在自然人投资者的定义上使用了与《中秘BIT》一样的措辞,但是该协定还专门规定了领土适用条款,“领土指:(一)就中国而言,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关税领土……”这就明确表明该协定的适用范围并不包括作为独立的关税区的香港。⒊香港有关缔约实践。为了确保香港的平稳过渡,填补因某些双边条约不再适用造成的空白,在过渡期内,由英国委托香港直接与第三国谈判缔结有关航空运输、投资促进与保护、移交逃犯等方面的条约。从1985年5月27日至1997年6月30日的过渡期内香港已与包括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在内的11个国家签订了BIT。回归后,经中央政府授权,香港政府又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韩国、英国、泰国等5国缔结了BIT。在与香港单独缔结BIT之前,这16个国家都已与中国政府签有BIT。就合格的自然人投资者而言,除了澳大利亚与中国缔结的BIT之外,其他15个中外BIT都与《中秘BIT》一样仅规定了国籍标准,而香港缔结的16个BIT则都规定“投资者,在香港方面系指1.在其地区内有居留权的自然人……”,也就是香港永久居民。倘若依据蔡叶深案仲裁庭的逻辑,既然中国早已与这15个国家缔结BIT,而这些BIT足以保护香港投资者的利益,似乎香港政府就没有必要大费周章再与它们单独签订BIT了。对此仲裁庭解释说:“香港自行缔结投资促进与保护协定的权力并不因中国政府已经缔结的BIT而受到影响。从历史上看,具有各国国籍的人都曾在香港居住。因此,香港政府才会实施旨在为了保护其居民在其他国家的投资的政策。”也就是说具有中国国籍的香港永久居民可以寻求中外BIT和香港缔结的BIT的保护,而不具有中国国籍的香港永久居民却只能寻求香港缔结的BIT保护。由于香港缔结的BIT不仅在数量上与中外BIT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保护水平也不完全相同,这无疑造成了香港不同国籍投资者之间的不平等,是极不合理的。另外,仲裁庭的解释逻辑还会造成条约适用和管辖权的冲突。例如,对于发生在香港投资者和德国之间的争议,该投资者即可因具有中国国籍可以依据《中德BIT》主张权利并将争议诉诸ICSID仲裁,而德国则可能因投资者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寻求《港德BIT》的保护,要求根据其中的仲裁条款要求将争议依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目前,蔡叶深案仍在审理过程中。无论案件实体问题如何裁决,仲裁庭认定其对本案享有管辖权的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下,香港在经济、经贸等领域享有缔约权,而中央政府缔结的条约也不必然对香港地区和香港永久居民适用。本案申请方蔡叶深作为香港永久居民,无权基于中央政府与秘鲁政府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诉诸ICSID仲裁。在ICSID机制下,仲裁裁决不是绝对终局的,有可能被专门委员会撤消。仲裁庭明显越权是裁决被撤消的理由之一,其中也包括仲裁庭对无管辖权的争端进行裁决的情况。因此,在仲裁庭就实体问题作出裁决后,秘鲁应据此提出撤消申请,据理力争。然而,本案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海外的香港投资者开始寻求国际法上的救济途径,保护自身利益。本案申请方之所以基于《中秘BIT》提出仲裁请求也是因为香港与秘鲁未达成有效的投资保护机制。倘若日后本案仲裁庭有利于香港投资者的裁决因缺乏管辖权而被撤消,虽然维护了法律上的正义,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遗憾。(转载自中国知网,文章载于《行政与法》2010年第6期)',)
提供中外双边投资协定对香港的适用问题会员下载,编号:1700774319,格式为 docx,文件大小为8页,请使用软件:wps,office word 进行编辑,PPT模板中文字,图片,动画效果均可修改,PPT模板下载后图片无水印,更多精品PPT素材下载尽在某某PPT网。所有作品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并拥有版权或使用权,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若您的权利被侵害,请联系963098962@qq.com进行删除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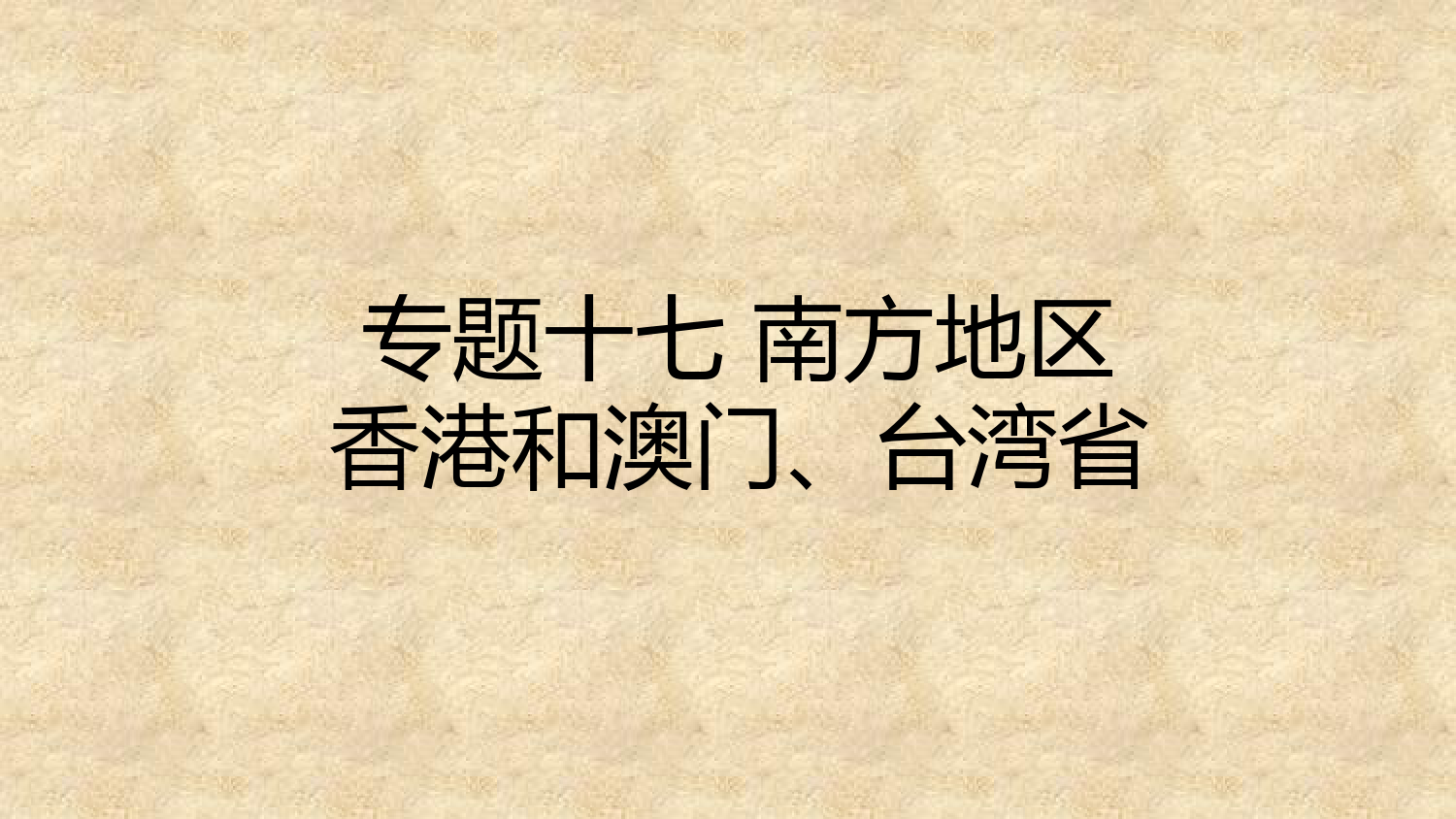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下载
下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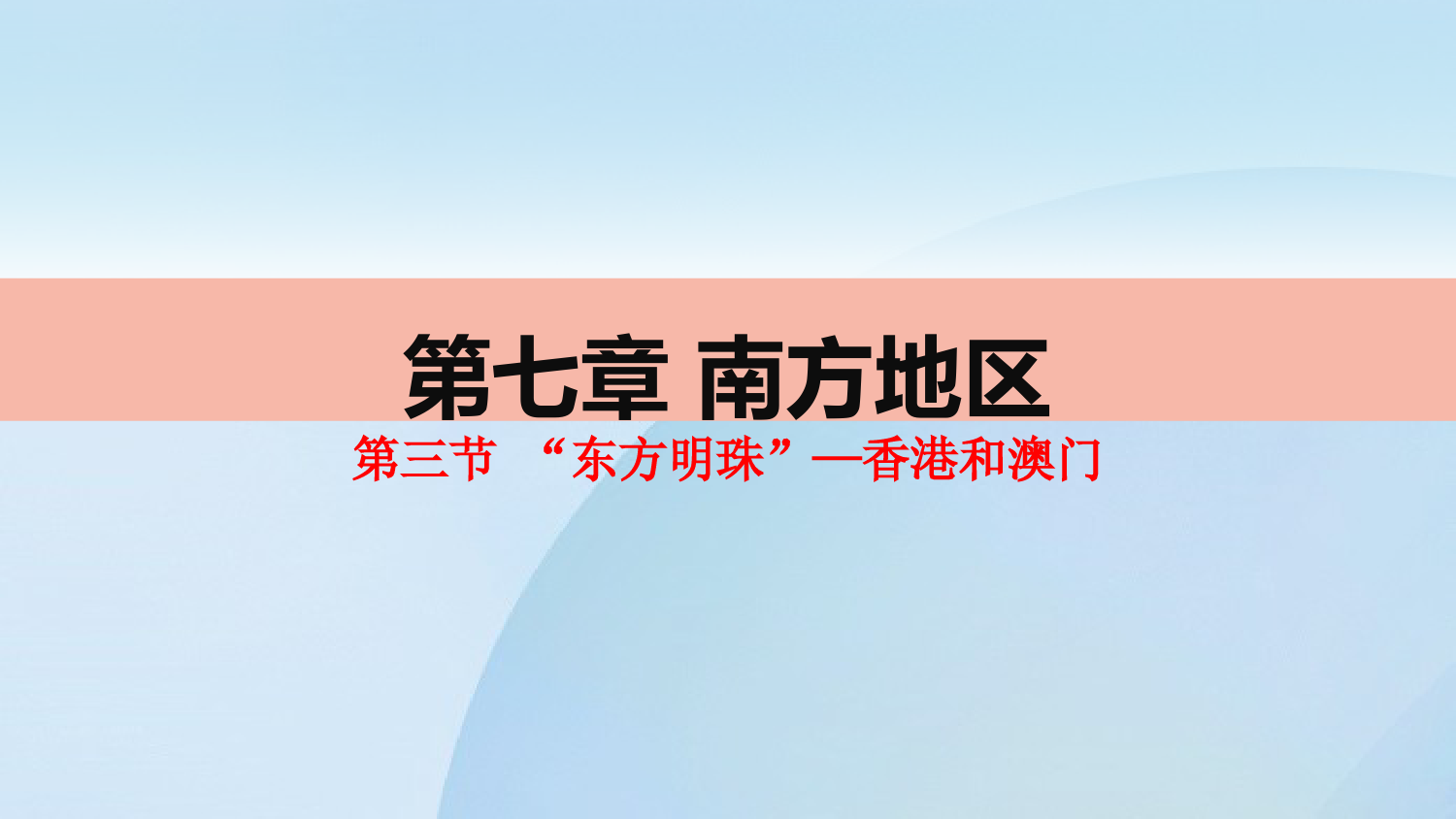 下载
下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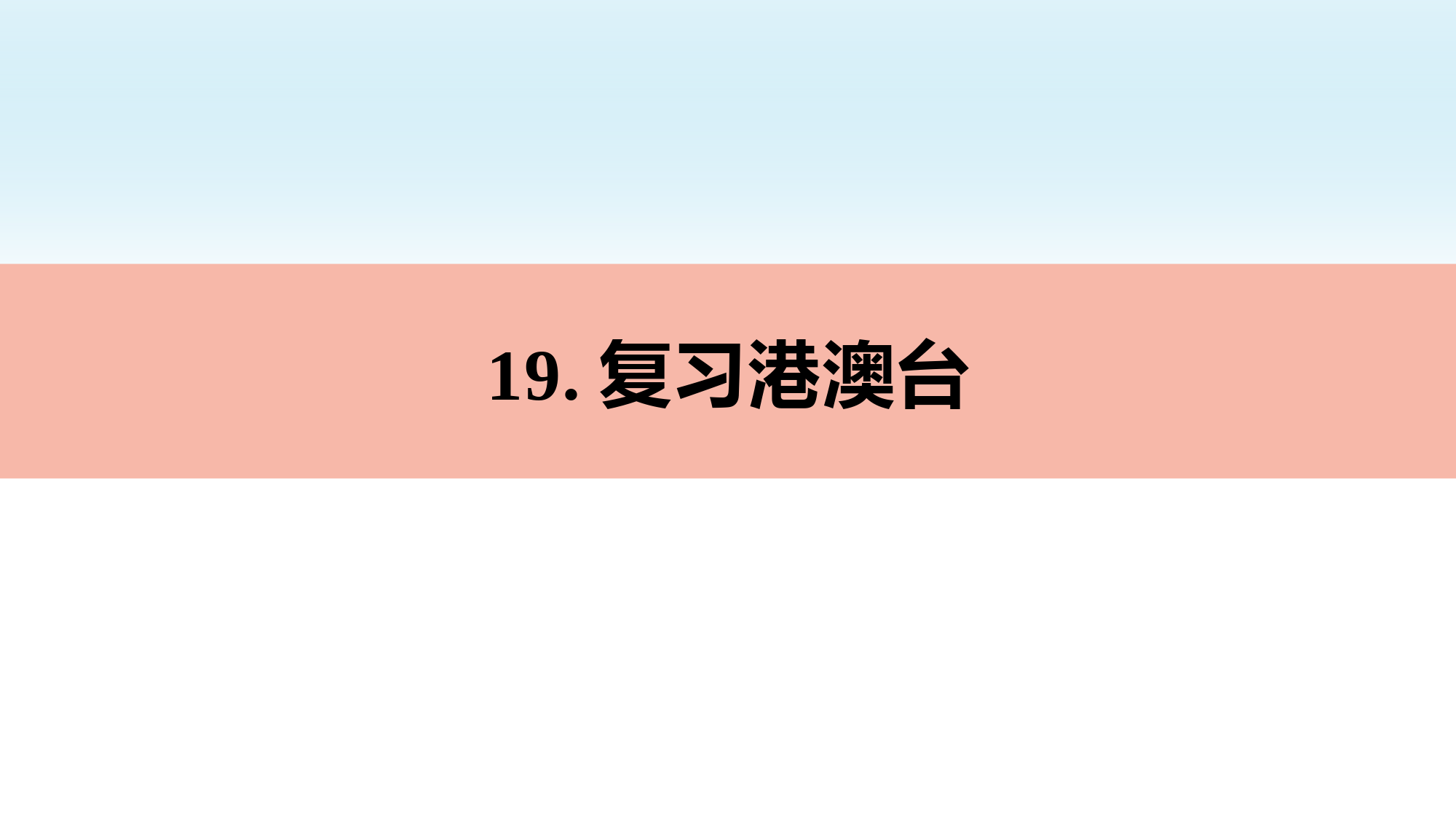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下载
下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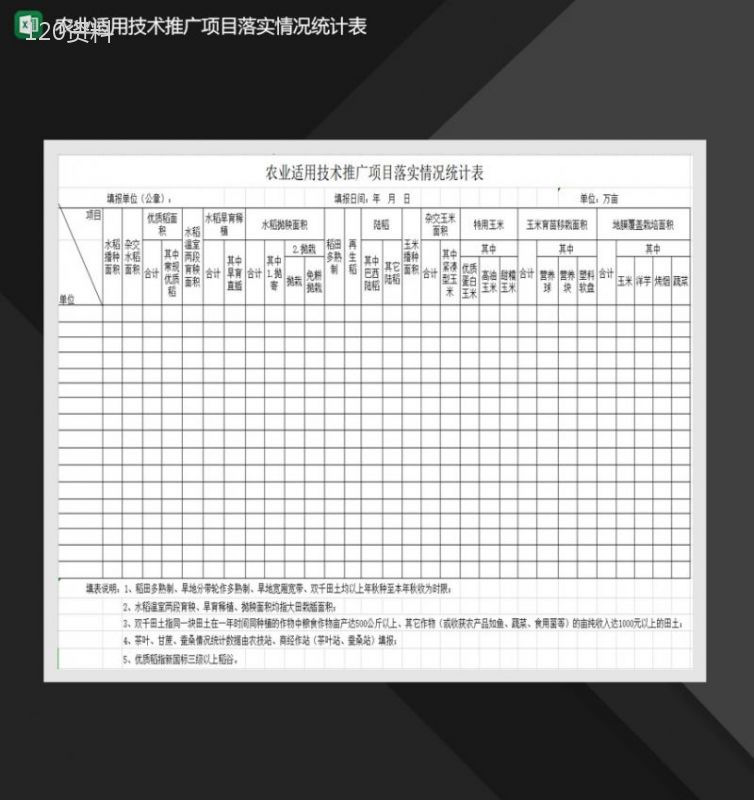 下载
下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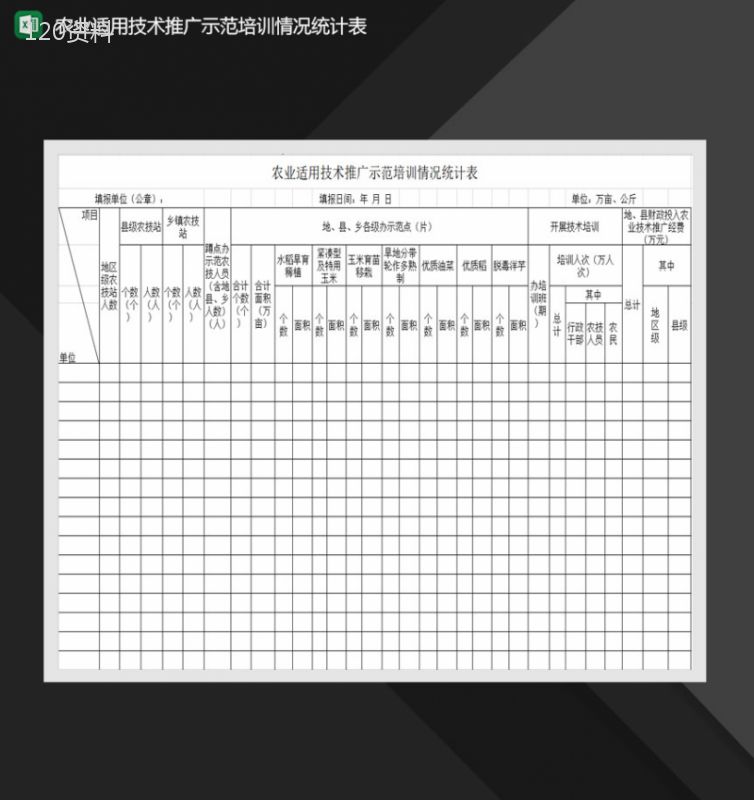 下载
下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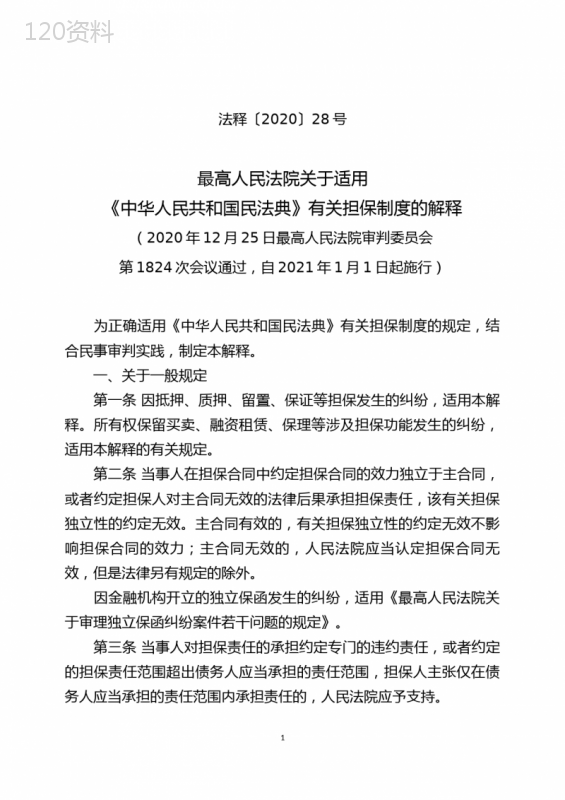 下载
下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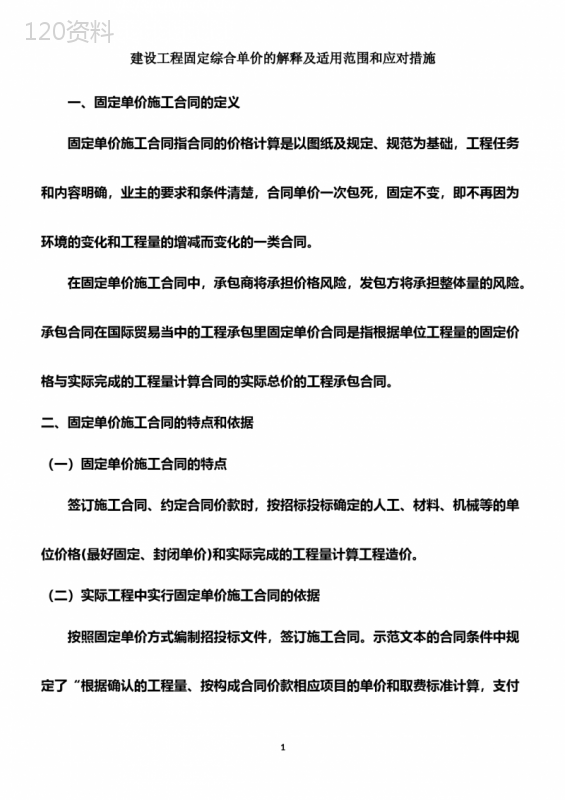 下载
下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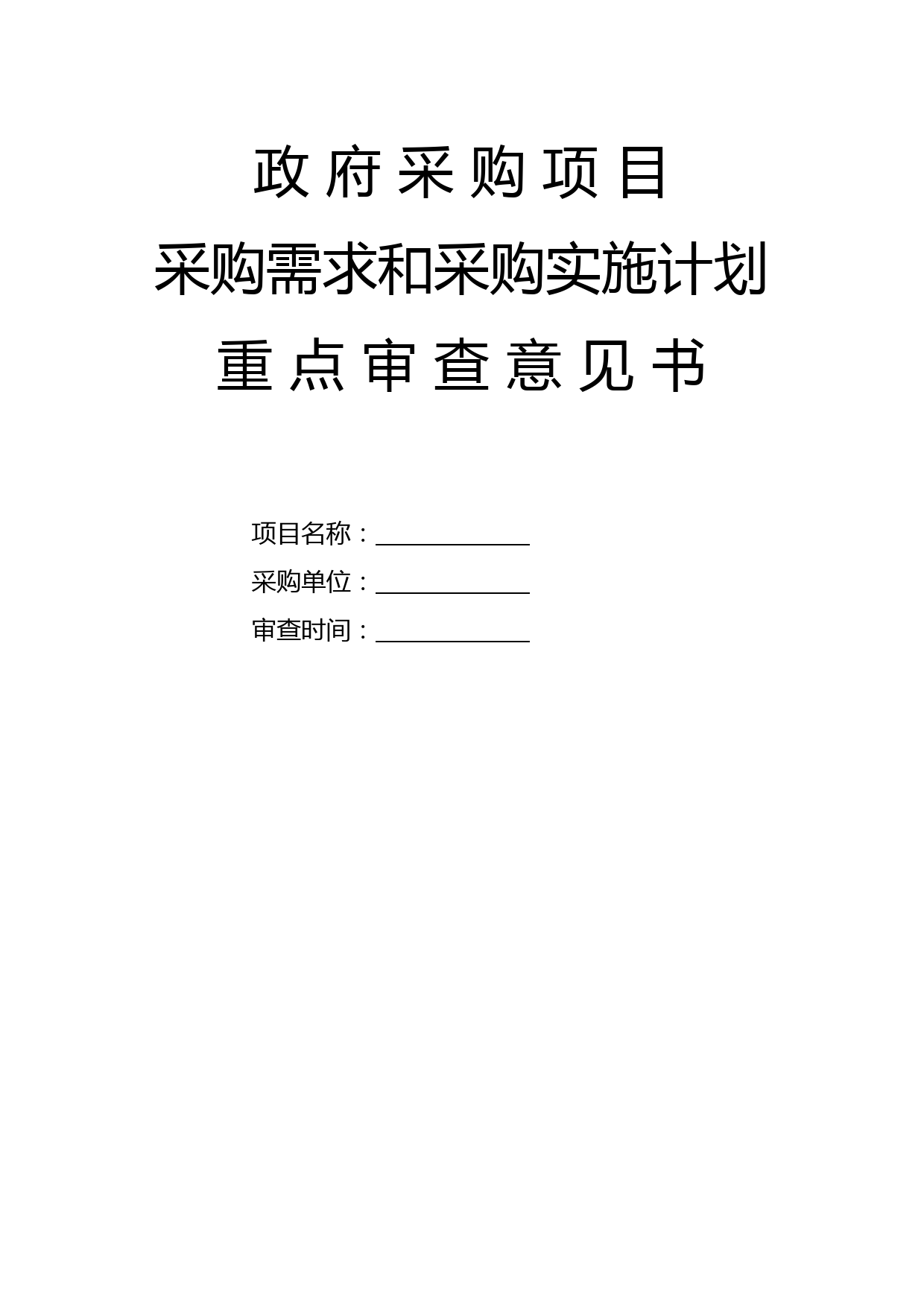 下载
下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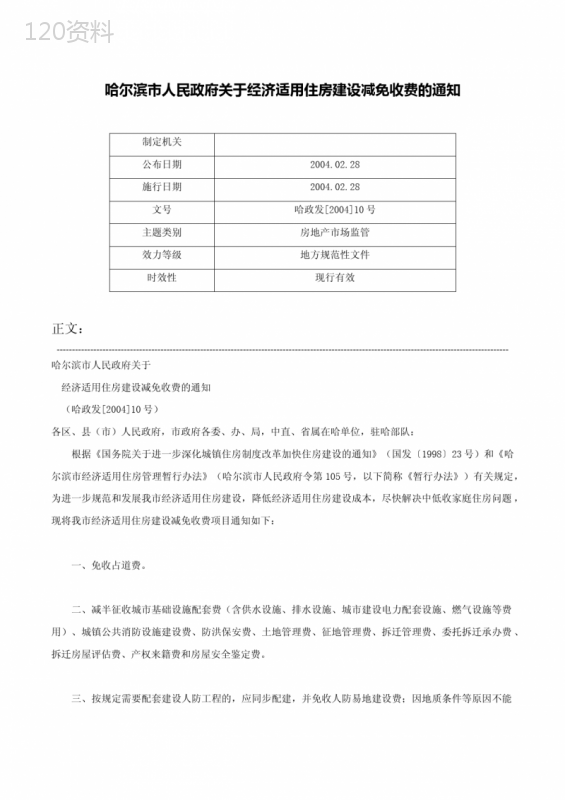 下载
下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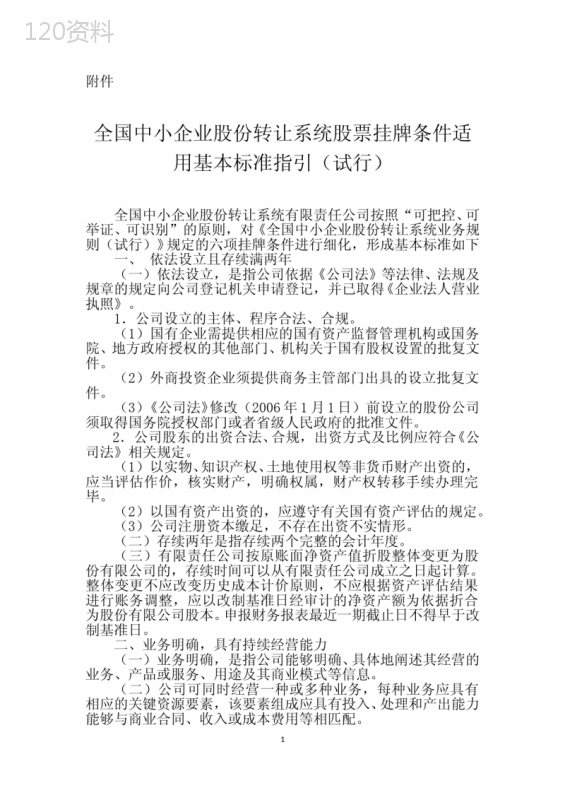 下载
下载